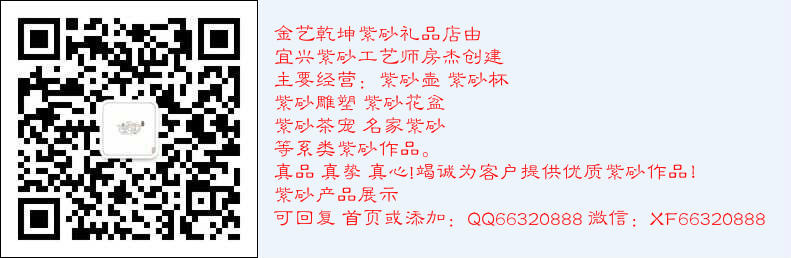蔣蓉原名蔣林鳳,1919年生於陶都宜興川埠潛洛六庄村的陶藝世家,11歲時隨父母做坯制壺,20歲時應聘至上海,與伯父紫砂高手蔣宏高(燕亭)一起制紫砂仿古器。1941年時,應聘到上海標準陶瓷公司任工藝輔導,1944年受聘於上海虞家花園,設計製作各種花盆。1945年回鄉制壺,1955年加入蜀山陶業合作社,製作國禮九件果品,1957年被評為“紫砂七藝人”(任淦庭、吳雲根、裴石民、王寅春、朱可心、顧景舟、蔣蓉)之一。1978年被江蘇省省政府任命為工藝美術師,1993年被國家授予“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稱號。1998年80歲高齡時還偶有創作。她的作品《荸薺壺》《芒果壺》分別被英國倫敦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和香港茶具文物館收藏。另一作品《枇杷筆架》作為國寶,被中南海紫光閣收藏。……

蔣蓉《百果壺》
紫砂真有秘笈嗎?蔣蓉的回答是坦然的:如果說紫砂真的有秘笈的話,那就是在紫砂藝人心中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對工藝的一種把握,而不是固定的方程式或分子式,更不是江湖上的咒語或解藥;那是因壺而異的工藝理念,是不可複製的心得天機。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說來就來了,卻頗具特質、令人心動的年代。中國人的生活在這十年里一直處於令人暈眩的急速變化之中”(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三聯書店出版)。然而,一路走來的中國紫砂在進人八十年代的時候,它的步履卻還帶着某種觀望、拘束的遲緩。這裡,我們不該忘記一位當時對紫砂走出國門起了重要作用的有識之士:羅桂祥。
羅桂祥是香港實業家,時任全國政協委員。此公名士風度,不喜歡燈紅酒綠,愛紫砂卻是成了癖的。別人金屋藏嬌、三妻四妾,他平生只喜品壺、養壺、藏壺。為了收藏紫砂,他不惜盪盡家產。紫砂竟然如命根子不離須臾。一九七九年秋天,羅桂祥悄悄來到宜興紫砂工藝廠,頗像一個探寶尋寶的俠士。他找了許多名手交談,這裡的人們還沒有從“文革”的餘悸里走出,說話都像溫吞水不冷不熱,讓這個熱心的香港人一時進退維谷。他聽說大陸習慣用開會來解決問題,於是請求廠方召集包括顧景舟、蔣蓉在內的二十餘名制壺高手開了一個“神仙會”。羅先生在會上拿出了一疊明清時期時大彬、陳鳴遠、陳曼生等紫砂名家的作品照片,請在場的制壺名手仿製這些作品。有人就說,我們做了誰來買啊?因為當時紫砂的海外市場還沒有開放,誰也不知道紫砂壺後來能比金子還貴。羅桂祥大聲說,我來收啊!只要作品做得好,我出高價收購。他還要求製作者落上自己的款印,說這才是藝術品。就這樣,羅桂祥作為“文革”後第一位推動並且訂製紫砂高檔產品的大客商、大收藏家而被寫進了紫砂歷史。在此之前,紫砂器均以品種來定價格,羅桂祥則開創了以製作藝人之名來定價格的規矩。這對推廣紫砂,將其提升到與金玉比價的高級工藝品地位,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在晚年蔣蓉的記憶里,當時她和羅桂祥的合作也是愉快的。羅桂樣笫一次上她的門來拜訪,信手拿出一把陳嗚遠的調砂《席扁壺》請她鑒定,這是陳鳴遠最具光貨造型特點並顯示非凡功力的作品之一。壺型極扁,適合沖飲綠茶。器型線面屈曲和諧,泥質用粗砂調製,配比恰當,肌理質感與形制十分和諧,目視有粗感,手撫則細膩。渾樸之中有峭拔之勢。
蔣蓉一見它就覺得眼熟,仔細一看不禁有些激動起來,原來這壺竟出自她自己——四十餘年前上海亭子間的林鳳姑娘之手。當時雖然不能在仿製名人的壺上打自己的印章,但她在每一把壺的壺把下端做了一個不易察覺的小小印記。生命如電如露,一切瞬間成空。這一把壺讓蔣蓉感慨萬端。世界就這麼小,人生就這麼巧合,全讓一把壺收進去了。羅桂祥也興奮不已,他執意要把這壺送還它真正的主人,而蔣蓉則堅持不肯接受已經屬於別人的心愛之物。最後是蔣蓉以自己的一把小佛手壺與之交換,成為紫砂收藏界的一段佳話。
桂祥的出現讓蔣蓉獲益匪淺。在他的大力推介下,蔣蓉的作品開始受到台灣、香港壺友的青眯。其時國門正漸趨開放之勢,與大陸骨肉相連的台灣同胞陸續登岸,而紫砂壺則是同胞相會最好的媒介和禮物之一。台灣地區雨水充足,盛產高山名茶而茶道興盛。
既有茶,豈可無壺?就是要用紫砂壺來泡,茶香才純正。茶客與壺迷也由此應運而生。蔣蓉的名字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台灣和香港、澳門的主流媒體上,人們把她看作是橫空出世的紫砂女藝人,她的田園式的清新風格使久居哺雜都市的人體驗到一種精神上的自然回歸。人們相信她日後將是不可限量的泰斗式人物,因此,收藏她的壺,會比收藏玉器字畫古董更有升值空間。
一些台港澳地區的壺商悄悄開進丁蜀古鎮,他們找個小旅館住下,一次次地上門拜訪意中的紫砂藝人,先付下數目可觀的定金,然後壺家會按照他們提供的壺樣製作茗壺,這些壺商把壺帶到台港澳地區出售,價格將是大陸上的十幾倍。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最好的紫砂壺就是這樣流向海外的,因為改革開放之初,大陸還沒有出現真正的富裕階層,消費水平較低,好東西自然流向海外。一些窮了一輩子的制壺名家則在這個時期迅速發達,在幾年之內就完成了他們一生的資本積累。
而蔣蓉卻一直未敢造次,她覺得自己拿着公家的工資,卻在家裡賣自己的茶壺,是一件說不過去的事。她老實了一輩子,她也不缺錢花。那些緊盯着不放的壺商便覺得這個老太太簡直不可理喻。直至有人假冒她的壺出售,她才如夢初醒。時代就像一個魔術師,它總是在變幻着老實人搞不懂的魔術。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紫砂茶壺漸漸變得不僅僅是茶壺,它和字畫、古董一樣,潮漲潮落,可以把人推向天堂,也可以把人打入地獄。
蔣蓉的一九八0年還有一件大事值得記述。這一年蔣蓉已經六十一歲,她身邊一直無人,年紀一天天大了,確實需要有個人做伴,同時也可以照顧她的起居生活。小勤是妹妹定風的孩子,以前經常來看她。有一次說到孩子的事,姐妹倆一拍即合,把小勤過繼給蔣蓉當女兒。這是個在農村長大的孩子,端莊、淳樸、勤快,這一年才十六歲,但也出落成一個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一年後,她中學畢業,廠里為了照顧蔣蓉,答應讓她來廠里上班。從此,蔣蓉的生活里就有了一個貼心的女兒兼徒弟。小勤第一次跟着她的蔣蓉媽媽到廠里來和大家見面的時候,所有的人都為蔣蓉高興。有人提議,既然做了蔣輔導的女兒,那就應該改個名字。叫什麼呢?呂堯臣老師(後來成為中國工藝美術大師)靈機一動說:“就叫藝華吧,你可要好好地把你媽媽的藝術才華學到手啊!”在旁的徐漢棠、汪寅仙老師(後來均為中國工藝美術大師)都說這個名字起得好,勉勵她早日成為一枝紫砂藝術之花。
華的到來確實給蔣蓉的單身生活增添了許多樂趣,而且,做母親的感覺讓蔣蓉在日後的創作中不知不覺地平添了更多的兒女情長。藝華一邊跟她學藝,一邊照顧她的生活,空閑時母女倆出去散散步,一起學唱流行的新歌,藝華能夠把一棵鹹菜也燒得有滋有味,開心的日子原本就這麼簡單。時間久了,她在向外地來的客商介紹藝華時,總是驕傲地說:“這是我女兒!”這時她就感到自己更像一個女人。
一九八三年春天,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來宜興主辦陶瓷造型培訓班,蔣蓉以六十五歲高齡成為該班年齡最大的學員。這個不脫產的培訓班每天晚上上課,張守智教授清晰地記得,開班第一天晚上,蔣蓉第一個早早來到教室,她安靜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就像一個虔誠的小學生。張守智很敬重她,說:“蔣蓉老師啊,您是老前輩了,應該您給大家上幾課才是。”蔣蓉說:“別客氣了,張教授,我是真心來學習的。”
是的,黑板和粉筆字以及朗朗的讀書聲,一直儲藏在她記憶的最親切部分。女兒蔣藝華是這樣回憶的:
她每天晚上把功課帶回家,在燈下看書做筆記,到半夜還不睡。她說,人老了,課堂上講的東西記不住,傳統的老藝人只有實踐,缺乏理論,眼界不免狹窄,怎麼能創新呢?這些課程安排得真好,學和不學,真是不一樣的。
理論培訓雖然只有三個月時問,但對蔣蓉的創作,卻有着較大的啟發。她在多種場合說過,這三個月勝過一年呢。
綜觀蔣蓉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壺藝創作,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類別:
1. 以瓜果植物入壺入器: 花貨肖形作品,大抵以神態見長,能否畢肖顯神、工而不俗,當是工匠與藝術家的根本區別。蔣蓉以荸薺、百果、石榴、荷藕、壽桃、松果、西瓜、芒果、佛手人壺,無不體現出她的一片天真爛漫的情趣。壺外的蔣蓉大氣素手,引一方天籟,點絳唇、藏溫婉、錦繡深處更傳淡泊;壺中的蔣蓉則如一個稚氣未脫的小女孩,她用一隻稚嫩的小手牽引你,領向她夢境一般的田園,飄香的是瓜果,紛飛的是蝴蝶,高歌的是牧童,奔流的是清泉。你在這裡找一找吧,那些失落的童真,憂傷的初戀,羞澀的少年夢……會重新叩訪你的心靈。聽,是蜀山古韻;聞,若蠡河潮聲;觀,乃煙雨幻化;品,化畫溪月色。白髮漁樵總是少,江南茶客依然多;何不共壺一柄,大雅紫砂而笑飲乾杯耳?
2. 以動物入壺人器: 玉兔、春牛、烏龜、青蛙、蛤蟆、飛蛾、螻蛄、螳螂……蔣蓉的壺藝創作,已經到了信手拈來,點石成金的地步。一切自然界的生命,一旦被她看中,即可幻化今生,縱身一躍而成為小小精靈,被永遠定格在紫砂藝術的天地之中。
3. 鼻煙瓶系列作品: 鼻煙壺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結晶。明末清初,鼻煙傳入中國,鼻煙壺應運而生,它集書畫、雕刻、鑲嵌、琢磨等技藝於一身,不僅是盛裝鼻煙的實用容器,更是供人玩賞和顯示身份地位的藝術佳品。蔣蓉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共創作紫砂鼻煙瓶、壺系列品種多件。其中,十件套葫蘆形紫砂鼻煙瓶精巧華美,形象逼肖,紫砂陶刻名家譚泉海見之甚喜,應蔣蓉之邀,在每個鼻煙瓶上刻下明秀的山水、遒勁的書法、吉祥的動物以及古樸的瓦當紋樣,使它們成為紫砂袖珍藝術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其他如荸薺、菱角、蘋果、竹節鼻煙壺則玲瓏小巧、實用耐看,令人愛不釋手。
4. 陶塑系列作品: 蔣蓉的陶塑造型功力在同輩藝人中堪稱一絕。其中蓮藕筆架為文房雅玩,自是妙思若神、形色俱佳;陶土假山則有黃賓虹筆意,逶迤蒼勁;水牛、獅子、老虎等動物陶塑,着力表現生命的伸展、張揚之美與動物的神態動感之美,以民間美術的鮮活意趣一掃學院派的拘謹之風。最具深意的是一件名為《邯鄲夢》的冬瓜陶枕,色澤青碧,一端花蒂、一端瓜蔓,兩端微微翹起,中間稍凹。陶枕乃我國傳統工藝中的珍品,宋代定窯孩兒枕尤為出眾。蔣蓉創作的冬瓜枕自然舒展,無矯飾之態。著名畫家程十發為之題名《邯鄲夢》,取唐代傳奇《枕巾記》中“一枕夢黃粱”之意,以冬瓜之清麗素樸醒人於俗世。陶刻名家譚泉海在枕上欣然命筆:“靜坐書齋讀文章,卧寢竹窗聽秋嵐。”
上世紀八十年代蔣蓉可圈可點的作品不勝枚舉,如果讓它們集合起來,簡直是一個龐大的紫砂兵團。就像一部被打開的書,我們已經讀到了它最精彩的章節。如果讓蔣蓉自己來選擇,在那麼多愛不釋手的作品裡選出幾件她最滿意的,也許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
但她最終還是會肯定地告訴你,《荸薺壺》和《西瓜壺》,還有《秋葉樹蛙盤》《月色蛙蓮壺》都是和她十指連心、與她的生命等量齊觀的不可割捨的經典之作。
《荸薺壺》創作於一九八一年。一直到八十七歲的晚年,蔣蓉在敘述創作這把壺的過程的時候,臉上還掩飾不了孩子一般的得意:“說穿了吧,我這把壺就是做給那些看不起花器的人看的。”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顧景舟已經是當代紫砂的領軍人物。他平時的言談舉止,總是會不自覺地流露對紫砂花貨作品的輕視。蔣蓉的脾氣,從來都是用作品來說話的。《荸薺壺》的壺身,是一件典型的光素器作品,而它的裝飾卻具有花器與陶塑兼工的特點。壺嘴與壺把的線條,如凌波仙子憑空一躍,有意想不到的洒脫與幹練;而壺身的裝飾,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點綴。它已經逾越了像與不像的窠臼,那種草根而不卑賤、雍容而不顯貴的氣度,是需要一種氣質來支撐的,一般的紫砂藝人怎可比擬呢?《荸薺壺》要告訴別人的正是這樣的一種理念,光素器與花器絕不是天敵,就像藝術不應有貴賤之分,而只有優劣之別;好東兩不怕兼容,好朋友應該共存。《荸薺壺》最後被英國人永久收藏於維多利亞艾伯特博物館,它代表中國,代表一個遙遠的東方民族的工藝秘笈。
《秋葉樹蛙盤》,一九八三年創作。秋天是容易讓人感懷的季節。古人說一葉知秋,蔣蓉正是從一張捲曲的樹葉造型人手,她設計了一隻小青蛙,趴在樹葉的一端,睨視着一隻可憐的小小飛蛾。它們本是一對天敵,但青蛙發現,在深秋蕭索的天氣里,這隻小小飛蛾就要嗚呼哀哉了,小青蛙會憐憫它嗎?它是否也感受到了一種生命易逝的悲哀?蔣蓉把所有的故事安排在一張樹葉的時空里,接下去小青蛙和小小飛蛾之間還會發生什麼故事呢?那肯定是一個美麗的童話了。飛蛾的命運牽動着蔣蓉的心。她愛這個弱小的即將離去的生命,她要賦予它以美麗,哪怕是短暫的一瞬。前前後後,她一共捉了一百多隻飛蛾,放在小瓶子里觀察臨摹,她熟悉它們的每一根筋紋,她甚至能感受到它們的呼吸。最後的一隻小小飛蛾就這樣定格在樹葉的底部,它是一隻吟唱的蛾,周圍蛙聲如鼓,像十面埋伏;天已崩,地欲裂,它依然吟唱,永遠吟唱。當它終於不再是活生生的飛蛾而已經是藝術品的時候,一位記者和它發生了一個小小的誤會,在一個陶藝展覽會上,記者用手去拍打它,以為它是偷偷跑進這藝術殿堂來的不速之客。它偷偷地樂不可支:“別怪我,是蔣蓉奶奶讓我這般真假難辨的呀。”
《西瓜壺》,一九八五年創作。又是一件光器式的渾圓佳構。許多媒體在報道此壺時,着重強調了蔣蓉一連多日冒着烈日酷暑,不顧嚴重的腿疾,和女兒藝華趕了幾十里地去西瓜地里寫生的情景。但在蔣蓉晚年的回憶里,寫生的經歷只是一帶而過,她說得最多的,是西瓜壺的表現手法。西瓜之圓,是圓潤飽滿之圓;西瓜之脆,乃清脆新鮮之脆;蔣蓉在泥料的配置上做了幾十次試驗。終於找到了最適合表現西瓜的色彩語言。一次,我採訪蔣蓉的時候忍不住提過一個問題:紫砂真有秘笈嗎?蔣蓉的回答是坦然的:如果說紫砂真的有秘笈的話,那就是在紫砂藝人心中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對工藝的一種把握,而不是固定的方程式或分子式,更不是江湖上的咒語或解藥;那是因壺而異的工藝理念,是不可複製的心得天機,你只能在更不是江湖上的咒語或解藥;那是因壺而異的工藝理念,可不是複製的心得天機,你只能在具體的作品裡尋找答案。把好東西用最好的方式表達出來,是所有的藝術家畢生追求的目標。蔣蓉的《西瓜壺》花紋清晰可愛,瓜藤、瓜蒂塑成壺嘴壺把,從壺身與壺把的連接處斜出一張墨綠的瓜葉,兩朵嫩黃的小花,呼應出一片鮮活靈動的氣息。它永遠像一首田園詩,在被千萬次朗讀後依然翠綠如生。此壺現藏於宜興陶瓷博物館。

《月色蛙蓮壺》,一九八九年創作。這是一件段泥作品,以寫實手法把自然界的蓮荷、青蛙、昆蟲集於一壺。原宜興陶瓷博物館館長、紫砂文化專家時順華先生這樣評介這件佳作 :
:
她巧妙地利用藕節組成壺嘴,荷葉梗與花梗絞纏扭為壺把,蓮蓬為壺蓋,上棲一青蛙為壺紐,壺身為盛開之荷花,花脈清晰、自然靈動。童心和天趣是蔣蓉創作的主題,她具有捕捉美的瞬間的天賦才華,又有一手微型雕塑的過硬本領,善於把大自然中的美麗和生活中的情趣融入壺中,開創了獨具風格的“蔣氏陶藝”。